歧屈与诗的交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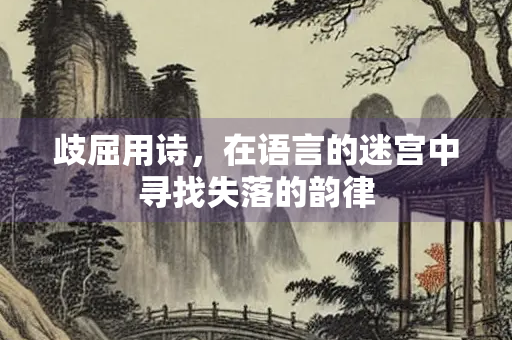
"歧屈"一词,本意为曲折、不直,引申为文字表达上的艰涩难懂,当我们将"歧屈"与"诗"并置,便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张力——诗歌本应是语言的艺术巅峰,是人类情感最精炼的表达,何以与"歧屈"产生关联?这种看似矛盾却又真实存在的现象,恰恰揭示了诗歌创作与解读中一个深层的悖论:最美的诗往往诞生于语言的边界,最动人的表达常常游走于理解的极限。
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诗无达诂"的观念由来已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这一观点,揭示了诗歌解读的多元可能性,诗歌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正是因为它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读者的经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生成,这种意义的"歧屈"不是缺陷,反而是诗歌生命力的源泉,当我们说"歧屈用诗"时,实际上是在探讨诗歌如何在语言的迷宫中既保持表达的深度与复杂性,又不失其艺术感染力。
古典诗学中的歧屈美学
中国古典诗歌中,"歧屈"的表达并非现代独有,李商隐的《锦瑟》一诗便是一个典型例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诗中意象跳跃,典故层叠,意义晦涩难明,却也因此成为千古绝唱,元好问曾评价李商隐:"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正是这种难以完全解读的特性,使得李商隐的诗作具有永恒的魅力。
宋代诗人黄庭坚提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创作理论,主张在继承前人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这种诗学观念本身就包含了对语言"歧屈"性的认可——诗歌不是对现实的直接摹写,而是通过语言的变形与重构,达到更高层次的真实,江西诗派追求"瘦硬"、"奇崛"的风格,实际上是在主动拥抱诗歌语言的"歧屈"特质,认为只有打破常规的表达方式,才能触及事物本质。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妙悟"说,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这种超越逻辑与常规语言的诗学理想,恰恰需要借助"歧屈"的表达来实现,当诗歌语言挣脱日常表达的束缚,进入一种半透明状态时,它既指向意义,又超越意义,既传达情感,又保留神秘,这种"歧屈"不是表达的失败,而是成功的标志。
现代诗歌中的歧屈实验
进入20世纪,随着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诗歌的"歧屈"特质被推向了新的高度,T.S.艾略特的《荒原》以其碎片化的结构、密集的典故和多语言混杂,创造了现代诗歌的"歧屈"典范,艾略特本人提出"客观对应物"理论,认为诗歌应该通过一系列意象、情境的并置,而非直接陈述,来表达情感,这种方法必然导致诗歌解读的多义性和困难性。
汉语现代诗中,卞之琳的《断章》以其简洁而多义著称:"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短短四句,构建了一个复杂的视角网络和意义循环,读者可以从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多种角度进行解读,这种"歧屈"不是表达的模糊,而是意义的丰富。
当代诗人北岛的诗歌也常常呈现出强烈的"歧屈"特征,他的《回答》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等诗句,通过悖论式的表达和意象的非常规组合,打破了习惯性思维,迫使读者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歧屈"是诗人有意为之的语言策略,目的是突破意识形态和常规思维的束缚。
法国诗人马拉美认为,诗歌的本质不在于说"花",而在于唤起"花"的缺席与在场之间的张力,这种诗学观念将"歧屈"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诗歌不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而是通过语言的"歧屈"创造意义的事件本身,现代诗歌对"歧屈"的探索,实际上是对语言本质和存在本质的双重探索。
歧屈的诗学价值与解读之道
"歧屈"在诗歌中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它对读者习惯性思维的挑战,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理论,认为艺术的目的是使对象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从而延长感知的过程,诗歌的"歧屈"正是通过打破自动化感知,恢复人们对世界的新鲜感受,当杜甫写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时,花与泪、鸟与心的非常规联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情感认知方式。
"歧屈"表达往往能够容纳更复杂的思想和情感,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而诗歌语言则是这个家中最本真的部分,当诗人试图表达那些难以言说的存在体验时,常规语言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唯有通过"歧屈"的表达——意象的跳跃、语法的变形、逻辑的中断——才能接近那种原初的体验,李贺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之所以震撼人心,正是因为其"歧屈"的意象组合直接唤起了战争场面的压迫感与壮烈感。
面对"歧屈"诗歌,读者需要采取不同于常规阅读的策略,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告诉我们,理解不是对作者原意的复制,而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过程,阅读"歧屈"诗歌时,我们不必急于寻找"正确"解释,而应允许自己在语言的迷宫中徘徊,体验多义性带来的丰富可能,正如宇文所安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中指出的,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可写性"——能够激发读者自己的创造性解读。
歧屈作为诗的宿命与荣耀
诗歌与"歧屈"的关系,犹如光与影的共生,没有"歧屈",诗歌将沦为平淡的陈述;只有"歧屈",诗歌又会失去与读者沟通的桥梁,伟大的诗人总是在清晰与晦涩、直白与婉转、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杜甫既能写"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明快,也能创作"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雄浑与"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的曲折。
"歧屈用诗"最终指向的是诗歌的本质问题——诗之所以为诗,正是因为它既在语言之中,又试图超越语言;既扎根于具体经验,又指向无限可能,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在《写作的喜悦》中写道:"在诗歌中,每一个'或许'都像树枝一样分叉。"这种由"歧屈"创造的分叉,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想象的翅膀,当我们学会欣赏诗歌中的"歧屈",我们实际上是在学习欣赏世界本身的复杂与丰富,学习在确定性与可能性之间舞蹈的艺术。
诗歌的"歧屈"不是缺陷,而是其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所在,它像一面多棱镜,将单一的白光分解为绚丽的色谱;它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通往语言秘境的多重门户,在这个意义上,"歧屈用诗"不仅是一种创作方式,更是一种生存智慧——承认世界与自我的复杂性,在不确定中寻找美的永恒。
本文地址: https://www.shuiwy.com/a/103444.html
文章来源:im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4-03-03im
2024-01-24im
2023-05-29im
2023-06-04im
2023-06-16im
2023-10-07im
2023-06-20im
2023-10-07im
2023-06-19im
2023-06-14im
2025-04-30im
2025-05-02im
2025-04-30im
2025-04-28im
2025-01-16im
2025-04-22im
2025-04-28im
2025-05-01im
2025-04-29im
2025-04-28im
扫码二维码
获取最新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