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咄嗟吾何叹"——这五个字像一记突然的鼓点,敲碎了陶渊明《饮酒·其十》表面平静的叙述节奏,当我们读到这声近乎脱口而出的叹息时,仿佛能看见诗人放下酒杯,眉头微蹙,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被某种深刻的思绪击中,这声叹息中包含着太多未竟之言:有困惑,有顿悟,有无奈,也有超脱,它像一道闪电,照亮了陶渊明诗歌中最为幽微的精神世界,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中国古代文人生命哲学的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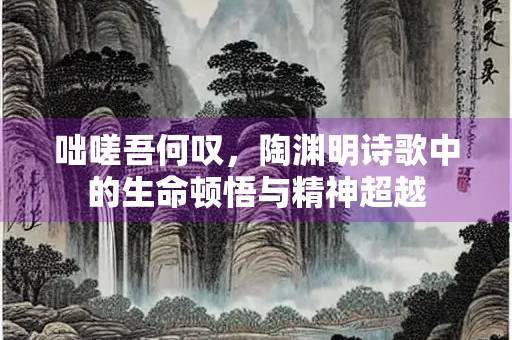
要真正理解这声叹息的分量,我们必须回到公元5世纪初的东晋末年,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桓玄篡位、刘裕崛起,政治舞台上刀光剑影;那也是一个精神觉醒的时代,佛教东传、玄学盛行,思想领域异彩纷呈,陶渊明就生活在这个矛盾交织的历史节点上。
作为没落士族子弟,陶渊明曾"猛志逸四海",却在二十九岁初入仕途后就不断经历"心为形役"的痛苦,他的五次出仕与归隐,实则是理想与现实不断撕扯的过程,当他在义熙元年(405年)最终辞去彭泽县令,写下"不为五斗米折腰"时,那不仅是一个政治选择,更是一次彻底的精神决裂。
《饮酒》二十首正是作于这次归隐之后,据学者考证,这些诗大约创作于公元416-417年间,当时陶渊明已五十余岁,经历了丧妹、火灾等一系列人生打击,对生命的思考愈发深邃,组诗虽以"饮酒"为名,实则"寄酒为迹",探讨的是更为根本的存在问题。
让我们先完整地看看这首诗:
"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 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 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 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 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 咄嗟吾何叹,古今同一躯。"
前六句叙述往事:诗人回忆年轻时曾远游至东海之滨,长途跋涉中遭遇风波阻隔,这里"东海隅"可能指他出任镇军参军时到过的曲阿(今江苏丹阳),也可能虚指极远之地,关键在"此行谁使然"的自问——表面是为饥寒所迫,实则暗示人生旅途的盲目性。
"倾身营一饱"四句展现转折:为温饱竭尽全力,却发现所需其实很少,这种发现带来顿悟:奔波劳碌并非生命真义,于是选择"息驾归闲居",这一决定与后来辞官归田形成呼应。
然后就是石破天惊的"咄嗟吾何叹"。"咄嗟"是象声词,模拟突然的叹息声,在晋代口语中表示顿悟或感慨。《世说新语》载谢安闻知淝水之战捷报时"默然无言",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这种强自抑制后的真情流露,与陶渊明的"咄嗟"异曲同工。
"古今同一躯"五字凝结着深厚的哲学思考,陶渊明在这里化用了《庄子·知北游》中"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的意象,将个体生命置于时间长河中审视,这种"齐物"视角消解了古今差异,也消解了个人遭遇的特殊性——无论王侯将相还是平民百姓,最终都归于同一具躯壳。
这种思想明显带有魏晋玄学的印记,当时"贵无论"盛行,文人多谈"有""无"之辩,陶渊明虽未直接参与清谈,但他的诗中随处可见玄理思考,在《形影神》组诗中,他让"形"主张及时行乐,"影"强调名节不朽,而"神"则提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超然态度。"古今同一躯"正是"神"的立场的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的哲学思考始终不离生活体验,与同时代那些沉迷清谈的士人不同,他的思想源自躬耕实践,在《归去来兮辞》中,他描述"园日涉以成趣"的生活,将玄理融入"植杖而耘耔"的具体劳作,这种知行合一的特质,使他的诗歌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生活温度。
"咄嗟吾何叹"标志着诗人精神成长的关键节点,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三重境界:
困惑的释放,在前九句的叙述中,诗人压抑着对人生意义的质疑,直到无法遏制而爆发。"咄嗟"这个象声词保留了情感的原初状态,比任何修饰语都更有力量,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陶诗之妙,正在其不经意处见真性情。"
认知的飞跃,从具体经历(远游、饥驱、归隐)到普遍真理(古今同一躯)的跃升,展现了诗人由个别到一般的思维能力,这种飞跃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直觉式的领悟,类似禅宗的"顿悟"。
精神的解脱,认识到"古今同一躯"后,诗人不再执着于个人得失,在《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的闲适背后,正是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正如苏轼评价:"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读有奇趣。"
陶渊明这种通过日常细节触发哲学思考的表达方式,开创了中国诗歌的新传统,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观察其影响:
在语言创新方面,"咄嗟"这种口语入诗的做法打破了当时骈俪文风的束缚,后来杜甫的"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苏轼的"噫吁嚱,危乎高哉"都延续了这种以声传情的传统。
在主题拓展上,他将玄言诗从抽象说理转向生活体验,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杨万里的"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都可见陶诗影子。
最重要的是精神品格的传承,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放、苏轼"人生如逆旅"的旷达,乃至现代作家汪曾祺的"人间草木"哲学,都延续了陶渊明这种将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态度。
在这个加速内卷的时代,陶渊明的叹息显得尤为珍贵,当我们被KPI追赶、被算法定义时,"古今同一躯"的提醒无异于一剂解毒剂,它至少给予我们三重启示:
简化生活的勇气。"少许便有馀"的发现直指消费主义的迷思,法国哲学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一个人的富有程度,等于他能够放得下的东西的数量。"这与陶渊明早在一千五百年前的实践遥相呼应。
超越成败的智慧,在"古今同一躯"的视野下,一时得失显得微不足道,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向死而生"的概念,认为只有直面生命的有限性,才能活出本真状态,陶渊明正是通过承认肉体局限,获得了精神自由。
回归本真的途径,陶渊明选择躬耕不是逃避,而是建构,他用诗歌和农事创造了一个意义世界,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发现:"人可以被剥夺一切,除了最后的自由——选择自己对境遇的态度。"陶渊明早用一生实践了这个真理。
"咄嗟吾何叹"之所以打动人心,正因为它捕捉到了人类共有的存在体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我们突然意识到生命的短暂与永恒、渺小与伟大,这种意识既带来刺痛,也带来解脱。
陶渊明没有停留在叹息中,在《饮酒》接下来的诗篇里,我们看到"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啸傲东轩下"的豪情,"不觉知有我"的忘境,一声"咄嗟"如同禅宗的"棒喝",打破了惯常的思维模式,开启了更为广阔的精神空间。
当我们今天重读这句诗时,那声叹息穿越千年依然鲜活,它提醒我们:在追逐外物的过程中,不要忘记停下来问一句"吾何叹";在丈量世界的同时,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同一躯"中的旅伴,或许,这就是陶渊明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在认识到生命有限性的同时,反而能更充分地活在当下。
接下来我们将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这首诗的内涵:
本文地址: https://www.shuiwy.com/a/107686.html
文章来源:im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
2026-01-12im
2026-01-12im
2026-01-12im
2026-01-12im
2026-01-12im
2026-01-12im
2026-01-12im
2026-01-12im
2026-01-12im
2026-01-12im
2024-03-03im
2024-01-24im
2023-05-29im
2023-06-04im
2023-06-16im
2023-10-07im
2023-06-20im
2023-10-07im
2023-06-19im
2023-06-14im
2025-05-06im
2023-09-01im
2024-01-10im
2023-08-10im
2025-04-22im
2023-08-26im
2024-01-09im
2024-01-08im
2024-01-09im
2024-01-09im
扫码二维码
获取最新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