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苏轼《定风波》中的"斜"字读音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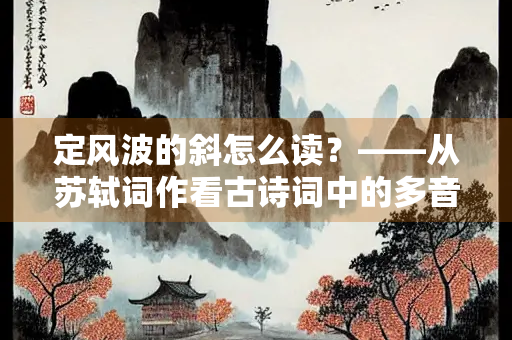
在中国古典诗词的阅读与吟诵中,多音字的正确发音一直是学界和诗词爱好者关注的焦点,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为宋词中的经典之作,quot;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一句中的"斜"字读音,近年来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个看似简单的字,却牵动着我们对古典诗词音韵美的理解与传承。
传统教学中,多数老师会按照现代汉语拼音将"斜"读作"xié",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读音一致,一些古诗词研究者和吟诵专家提出,为了保持诗词的韵律美,此处应读作古音"xiá",以与上句的"醒"(xǐng)、"冷"(lěng)和下句的"迎"(yíng)形成押韵效果,这种观点认为,苏轼创作时是按照当时的语音系统来押韵的,现代读者应当尊重原作的语言面貌。
这一争议实际上反映了古典诗词传承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当古音与现代读音发生差异时,我们应当如何取舍?是完全遵循现代汉语的规范读音,还是适当保留古音以求韵律和谐?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单个字的发音,更涉及我们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态度与方法。
从语言学角度看,"斜"字在中古时期属于"麻韵",拟音为/*zia/,与"家"、"花"等字同韵,随着语音的历史演变,北方话中麻韵的二等字(如"家"、"牙")与三等字(如"斜"、"些")发生了分化,而南方一些方言则保留了更古老的读音,主张读"xiá"的观点有其历史语音学的依据。
语言是活的、不断变化的系统,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其读音规范已经确立,这就产生了学术考据与现实应用之间的矛盾,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在尊重历史与适应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既不能完全忽视古音的历史存在,也不必过度强调复古而影响现代人的诗词欣赏。
二、"斜"字的音韵演变:从古音到现代的轨迹
要深入理解"斜"字读音的争议,必须追溯其在汉语音韵史上的演变过程。"斜"字最早见于《说文解字》,许慎解释为"抒也,从斗余声",属于形声字,在中古音韵系统中,"斜"属于假摄麻韵三等开口平声邪母字,拟音为/*zia/,与"邪"、"耶"等字同音。
隋唐时期,《切韵》、《广韵》等韵书反映了当时的语音系统,"斜"与"花"、"家"、"沙"等字同属麻韵,可以互相押韵,这在唐诗中有大量例证,如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都显示了"斜"与"花"、"家"的押韵关系。
宋代语音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古的麻韵开始分化,根据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和朱熹《诗集传》中的叶音注,可以推测北宋时期"斜"字仍保留着与"家"、"花"同韵的读音,苏轼作为北宋文人,其词作中的用韵应当符合当时的语音习惯,这也是主张"斜照"读"xiá照"的重要依据。
元明以后,北方话语音系统发生重大调整,中古的麻韵三等字(如"斜"、"些"、"耶")逐渐与二等字(如"家"、"牙"、"沙")分离,演变为现代普通话中的"ie"韵母,南方方言如粤语、客家话、闽南语等则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古音特征,粤语中"斜"读作"ce4",仍与"车"、"些"同韵,与普通话有明显差异。
明清时期的韵书如《洪武正韵》、《音韵阐微》已经反映了这种语音变化,"斜"字的读音与现代日趋接近,民国时期制定的"老国音"和新中国成立后确定的普通话标准音,最终确立了"xié"这一现代读音,这一漫长的音变过程,正是造成今天读音争议的历史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语音演变是渐进的、不均衡的过程,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中,变化速度可能不同,某些文人可能出于守旧或押韵需要,刻意保留古音读法,而普通百姓则更快接受新读音,这种差异在分析具体作品时需要谨慎考虑。
三、诗词格律与押韵要求:艺术形式的特殊考量
古典诗词作为一种高度形式化的文学艺术,其格律和押韵要求常常超越日常语言的规范,形成独特的语音体系,苏轼《定风波》作为一首词,遵循着特定的词牌格律,其押韵和平仄安排都有严格规定。
《定风波》这一词牌双调六十二字,上阕五句三平韵,下阕六句四仄韵,苏轼此词上阕押"声"、"行"、"生"、"迎"四韵,下阕押"马"、"怕"、"下"三韵,按照现代普通话,"醒"(xǐng)、"冷"(lěng)、"迎"(yíng)三字韵母分别为"ing"、"eng"、"ing",已不完全押韵,若将"斜"读作"xiá",则"醒"、"冷"、"斜"、"迎"四字在主要元音上更为接近(i、e、a、i),形成一种近似押韵的效果。
从诗词创作的角度看,宋代词人用韵主要依据当时的实际语音,而非严格遵循《广韵》系统,北宋已经出现了"诗韵"与"口语"分离的现象,文人作诗填词时会参考韵书,但也会根据实际语音有所变通,苏轼作为四川人,其语音可能带有一定方音色彩,但大体上仍遵循中原雅音。
值得注意的是,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最初是配乐演唱的,在演唱过程中,某些字音的发音可能因旋律需要而有所调整,这与单纯的朗读有所不同,现代人已无法确知宋代词乐的具体唱法,但可以推测音乐性对字音处理有一定影响。
明清以后,随着词乐的失传,词逐渐成为案头文学,其读音也随当时语音而变化,清代词学家万树《词律》和戈载《词林正韵》在讨论词牌格律时,已经按照清代的语音系统来分析押韵,不再拘泥于宋人读音,这一现象提示我们,诗词的读音传统本身也是不断演变的。
当代吟诵实践中,如何处理这类古今音差异成为一个实际问题,完全按照现代普通话读,可能破坏原作的韵律美;过度追求古音,又可能造成理解障碍和做作感,一些吟诵专家采取折中办法,在关键押韵字上适当保留古音,其余部分使用现代读音,既保持韵律和谐,又不至于过于脱离现代语言环境。
四、学界观点与教学实践:多元视角下的读音选择
面对"定风波斜怎么读"这一问题,语言学界、文学研究界和教育界存在多种观点,反映了不同学科视角下的考量差异。
语言学家普遍强调语言的历史发展和现代规范,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中指出,语音演变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现代人学习古典诗词应当以现代普通话为标准,不必刻意复古,他也承认在分析古代韵文时,了解古音有助于理解原作的艺术特色,周祖谟等学者则更注重方言中保留的古音材料,认为这些活的语言化石对研究历史音变有重要价值。
文学研究者往往更关注诗词的艺术完整性,叶嘉莹先生在论述诗词吟诵时强调"声情之美",认为适当的古音保留有助于传达作品的音乐性和情感内涵,她主张在关键韵脚字上可以采用"叶音"读法,即临时改变某字的读音以求押韵,这种方法源自朱熹《诗集传》,而袁行霈等学者则持相对保守态度,认为过度强调古音可能影响诗词的现代传播。
教育实践领域面临更实际的问题,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通常严格按照现代汉语拼音教学,避免给学生造成混淆,人教版语文教材对《定风波》中"斜"字标注为"xié",体现了这一原则,而在大学中文系和专业诗词课程中,教师可能会介绍古音知识作为背景,但不要求改变现代读音。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和诗词热,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折中方案,一些诗词爱好者组织提倡"双轨制":日常阅读使用现代读音,专门吟诵活动时可适当采用古音,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在处理这类问题时,通常遵循现代规范,同时通过专家点评介绍相关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区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也有差异,在保留较多古音的方言区,如粤语地区,用方言吟诵古诗词时自然保持了许多古音特征,不存在"斜"字读音争议,而在北方方言区,由于语音演变更为剧烈,古今音差异问题更为突出。
综合各方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共识:在普通教育和大众传播中,应坚持现代汉语规范读音;在专业研究和艺术表演领域,可以适当介绍和运用古音知识;最重要的原则是保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理解不同选择的合理性。
五、文化传承与创新平衡:面向未来的读音策略
"定风波斜怎么读"这一看似微小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性挑战,在全球化、数字化的今天,如何既保持文化本真性又促进创新发展,是我们必须思考的课题。
从文化传承角度看,古典诗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其语言形式与内容意境构成有机整体,最大限度地还原和理解原作的语言面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把握传统文化精髓,特别是诗词的韵律美,是其艺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当的古音保留可以增强审美体验。
从现代应用角度看,语言是交流工具,过度强调古音可能造成沟通障碍,不利于古典诗词的普及和传播,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其规范性应当得到尊重,许多现代诗人创作旧体诗词时,已经按照现代语音押韵,这体现了语言艺术的当代发展。
在实践层面,我们可以采取分层次、多样化的策略:
在教育体系中,基础教育阶段坚持现代读音标准,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中介绍古音知识,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既保证了规范性,又为有兴趣者提供了深入学习的机会。
在媒体传播中,主流平台采用现代读音,专门的文化节目和出版物可以尝试多元化的呈现方式,同一首诗词可以用现代读音和模拟古音分别演绎,让观众比较体验。
在学术研究中,继续深入探讨历史语音和方言材料,为读音问题提供更丰富的参考依据,数字技术如语音合成和数据库建设,可以帮助复原和展示不同时期的读音面貌。
在艺术创作中,鼓励创新性的演绎方式,现代作曲家为古诗词谱曲时,可以灵活处理字音与旋律的关系;戏剧表演中可以根据角色设定和风格需要,选择适当的读音方式。
最重要的是培养公众对语言变化的理性认识,通过科普文章、讲座等形式,说明语音演变的自然性和必然性,减少对"正统读音"的偏执追求,理解语言的生命在于使用和变化,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诗词艺术。
回到苏轼的《定风波》,无论选择"xié"还是"xiá",都不应影响我们对这首词精神内涵的领悟。"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超然态度,或许正是面对读音争议时应有的智慧:既尊重传统,又顺应变化,在坚守与变通之间找到平衡。
六、超越读音:回归诗词的精神本质
在深入探讨"斜"字读音之后,我们或许应该回归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阅读古典诗词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精确复制古人的发音,还是为了汲取其中的思想智慧和审美愉悦?
苏轼《定风波》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传达了一种面对人生风雨的豁达态度。"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精神境界,远比某个字的读音更重要,过度纠结于语音形式,反而可能遮蔽作品的精神光芒。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注重"得意忘言"的思维方式。《庄子·外物》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语言作为表意工具,其价值在于传达的思想和情感,而非形式本身。
从历史角度看,伟大的文学作品总能超越时代的语言局限,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不会因为古今读音差异而减损其思乡之情;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会因现代人不懂"床"的古义而失去其静夜之思,同样,苏轼的"山头斜照却相迎"无论"斜"读何音,都能让我们感受到雨过天晴的欣然。
在当代社会,我们或许应该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诗词欣赏观,可以了解古音知识作为文化背景,但不将其视为不可逾越的规范;可以探讨读音问题作为学术话题,但不因此影响普通读者的欣赏乐趣;可以尝试不同读法作为艺术实验,但不将其绝对化为唯一正确方式。
古典诗词的生命力在于与现代读者的心灵对话,当我们读到"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时,能否从中获得面对人生起伏的智慧,远比能否准确发出每个字的古音更为重要,这种精神的传承,才是文化传统的真正延续。
在结束这篇关于"定风波斜怎么读"的讨论时,我们不妨记住:读音问题值得探讨,但不应成为欣赏诗词的障碍;语言形式需要研究,但不应掩盖作品的精神价值,在尊重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心灵的开放与自由,或许才是对待古典诗词最健康的态度。
本文地址: https://www.shuiwy.com/a/103658.html
文章来源:im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6-01-13im
2024-03-03im
2024-01-24im
2023-05-29im
2023-06-04im
2023-06-16im
2023-10-07im
2023-06-20im
2023-10-07im
2023-06-19im
2023-06-14im
2023-05-25im
2025-04-18im
2023-05-25im
2025-04-18im
2023-06-14im
2025-04-18im
2023-07-13im
2025-02-09im
2023-06-23im
2025-04-17im
扫码二维码
获取最新动态
